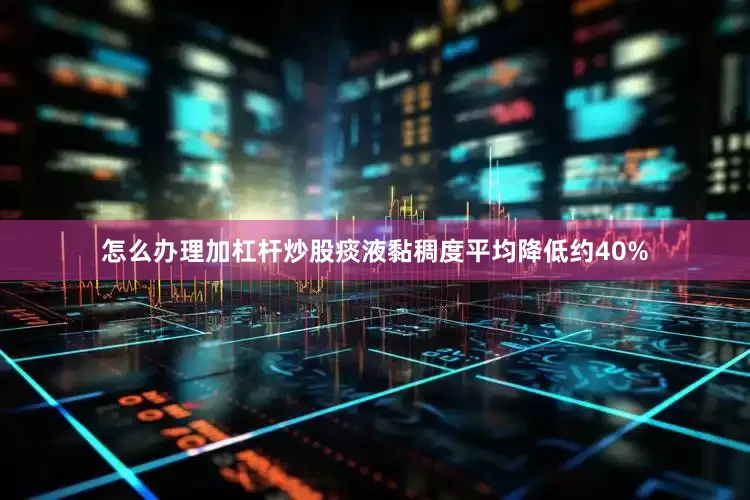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彼此最大的邻国,共享着一条绵长的边界线,且两国间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数百年来,中俄之间的外交历程对俄罗斯的东方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塑造了当今蒙古高原及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1526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实现罗斯各邦统一,并自封沙皇,直至1917年沙俄因二月革命而瓦解的391年间,沙俄始终秉持着坚决的对外扩张策略。
在北方地域,沙皇派遣探险队伍,成功地将领土延伸至摩尔曼斯克乃至北极区域。至于西面,俄罗斯历经利沃尼亚战争、大北方战争及拿破仑战争的洗礼,成功占据了波罗的海南岸与西岸的广大区域,其中包括芬兰,并且,通过三次对波兰的瓜分,俄罗斯获取了波兰的大面积领土。

俄罗斯在西南地域,历经数百年与波兰、土耳其及波斯的战争较量,成功掌握了现今乌克兰、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广阔地域,其影响力亦延伸至巴尔干半岛。
沙俄势力在东方扩张的进程中,首先驯服了位于东南方向的诺盖人、巴什基尔人等游牧族群,随后进一步将哈萨克、布哈拉、浩罕等国家纳入其统治之下,从而牢牢掌控了中亚地区的广袤草原与肥沃绿洲。
在《书名号》所述的时代背景之前,人类间的交往与接触已初具规模。彼时,虽未步入近代的门槛,但不同地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已通过商贸往来、文化传递等多种形式悄然展开。这些早期的接触,虽不如近代以后那般频繁与深入,却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伏笔,奠定了人类相互认知与合作的基础。
在东方,俄罗斯的传统疆域原本局限于卡马河与伏尔加河的西侧。然而,在瓦西里三世及其继承人伊凡雷帝的统治时期,沙皇俄国逐步征服了由金帐汗国分支所建立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与喀山汗国。此后,沙俄更是凭借武装探险活动以及哥萨克的侵袭,将西伯利亚汗国纳入其版图之中。

至17世纪,效命于沙皇的哥萨克族群凭借西伯利亚错综复杂的水网体系,乘舟深入黑龙江流域。在哈巴罗夫、波雅尔科夫、斯捷潘诺夫等人的引领下,俄国凭借武力手段,使得当地的野人女真、达斡尔等部族臣服,其势力范围逐渐扩展至中国的边界地带。
1618年,俄国沙皇亦派遣了一支使节团至北京,意在觐见明朝的万历帝。然而,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及献礼上的不妥之处,该使节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至1656年,沙俄已在黑龙江流域构建起一系列殖民基地,并着手构筑防御工事之际,一支源自尼布楚的沙俄使节团抵达中国,觐见了顺治帝。此次会面,双方借助蒙古语及西欧语言作为沟通桥梁,通过翻译实现了官方层面的首次交流。

彼时,清朝自视甚高,视自身为天朝上邦,而将沙俄轻视为如同喀尔喀蒙古般的微不足道之辈,对沙皇冠以“察罕汗”之名。再者,因使团乃是穿越蒙古戈壁抵达,未取道黑龙江一线,故而清朝对使团所提及的“俄罗斯帝国”与在黑龙江一带肆意劫掠的哥萨克人实为同一势力的事实,全然不知。
俄国在当时展现出极度傲慢的态度,其初始观念中,清朝不过是一个规模稍大的蒙古与通古斯部落集合体。他们将清朝皇帝称为“博格达汗”,并抱有期望,即清朝君主能仿效其他西伯利亚部族,迅速向沙皇俯首称臣并献上贡品,尤其是毛皮等物资。

然而,不久之后,哥萨克人在黑龙江流域的侵扰活动日益加剧,导致清军与其的冲突规模持续扩大,这使清朝深刻认识到其与沙皇之间的真实关系。鉴于此,清朝随即强化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并在《1685年》与《1686年》的两次雅克萨战役中,成功抵御了以哥萨克人为主体的沙俄侵略者的进攻。
沙俄至此方意识到,中国乃是一个地域广袤、国力强大的东方大国。鉴于彼时沙俄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难以向东方调动,俄国因此暂且采取了妥协策略,与中国缔结了《尼布楚条约》。随后,在1775年,双方再次签署了《恰克图条约》。在此阶段,沙俄对清朝表现得相对克制,未再引发重大争端。

然而,自1860年起,俄国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展现出了其贪婪的本性。
在《书名号》所提及的情境中,存在着侵吞与蚕食的现象。这些行为如同蛀虫般逐渐侵蚀着资源,将其一点一滴地据为己有。侵吞者明目张胆地占取不应得之物,而蚕食者则更为隐蔽,他们缓缓消耗,直至将目标完全消耗殆尽。这两种行为,无论是公然进行还是暗中操作,都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和制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朝的衰弱逐渐为国际社会所共知,俄国亦洞察了清朝的实际状况。随之而来的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清朝在对外方面需应对鸦片战争及中法战争的挑战,对内则需平定广西会党、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西北回乱以及阿古柏势力等一连串的敌对势力,真可谓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

在此期间,俄罗斯持续地将囚犯流放到远东地区,并积极组织移民活动,旨在促进西伯利亚与中亚地区土著居民的俄化进程,同时增强对这些区域的掌控力。其对西伯利亚与中亚的经营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在黑龙江北岸,彼时该地区的人口已构成以俄罗斯移民为主的多数群体。
同时,俄国在50年代遭受了克里木战争的挫败,加之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系列改革,使得俄国迫切需要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并弥补战争所带来的损失。
在此情境下,俄国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视其为觊觎的目标。
1858年,在清军深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察觉清朝对北方防御力不从心,遂亲自带领300名哥萨克士兵,乘坐2艘装备火炮的舰艇,在黑龙江流域肆意巡游,表面上宣称“协助中国抵抗英军”,暗地里却派遣使节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无理要求,强迫清朝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全部领土,并提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应成为“中俄共同管理”的区域。

奕山最初拒绝了提议,随后穆拉维约夫在江边连续数日炮声隆隆,致使黑龙江南岸民众惶恐不安。加之俄国提出要求之际,恰逢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国家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
故而,奕山最终迫于俄国的强压,暗中与俄国缔结了《瑷珲条约》。穆拉维约夫因替沙皇拓展疆土立下功劳,被授予“阿穆尔伯爵”(即黑龙江伯爵)的封号,其形象后来还被镌刻于俄罗斯的钞票之上,与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一道,被尊为俄国的“民族楷模”。
1860年,在英法联军已在战争中击败清朝,且清朝向俄国求助以进行调停谈判的背景下,俄国进一步要求清朝割让乌苏里江一带的所谓“中俄共管区域”。清廷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妥协。随后,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并正式确认了此前《瑷珲条约》的效力,这一举动导致中国丧失了日本海与鄂霍次克的出海权益,而俄国则借此机会获得了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

自《北京条约》签署之际起,沙俄再度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地区。通过构筑防御工事及推动民众迁徙的手段,俄国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展至巴尔喀什湖周边区域。在《北京条约》商定过程中,虽提出中俄双方需联合勘定西北疆界,然而俄国却单方面主张在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之间采取“中线划分”的方式,对此,清廷同样予以拒绝。
1863年,沙俄派遣军队向边境推进,步步紧逼塔尔巴哈台、伊犁及科布多等地区。彼时,西北疆域的南疆、迪化乃至陕甘地带均陷于战火之中。清军因确实无力抵御,只得再度与俄国签订《勘分西北边界条约》,无奈割让了包含巴尔喀什湖、斋桑湖、特穆尔图湖等众多湖泊在内的大面积领土。

1871年,沙俄见有机可乘,利用新疆局势动荡之际,以“协助清朝守卫边疆”为幌子,侵占了伊犁地区。直至1878年,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后,沙俄才被迫放弃伊犁。然而,作为代价,中国又失去了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
依据相同的逻辑进行计算,晚清时期,俄国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的土地面积高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
然而,沙俄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当时沙俄国内还盛行着一种名为“黄俄罗斯主义”的思想。俄国宫廷亦策划了一个名为“黄俄罗斯计划”的方案,其核心意图在于将长城以北的地区转变为如同“小俄罗斯”(现今乌克兰)般的区域,进而将其纳入帝国的疆域之中。
基于此背景,1896年,沙俄利用中国甲午战争失利之机,假借防范日本之名,与清朝私下缔结了《中俄密约》。依据该密约条款,清朝名义上成为俄罗斯的“军事盟友”,然而,鉴于清朝国力孱弱,实则无力与俄国实施“联合防御”。由此,俄国得以将西伯利亚铁路扩展至中国领土,并享有了在该铁路沿线部署兵力、输送军事物资的权益。

1900年,俄国在参与八国联军行动的同时,再度调集13.8万兵力,分六路向东北地区发起进攻,几乎将包括奉天、长春、珲春等在内的东北重要区域悉数占领。事后,俄国与清朝政府签署了《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并一度在东北地区设立了总督职位,意在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然而,由于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对,俄国被迫放弃了这一企图。同年,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俄国很早就认识到了掌控蒙古地区的关键性,这一点不容忽视。俄国明确了解到清朝与喀尔喀蒙古间存在的分歧,并且意识到藏传佛教在蒙古民众中的深远影响。基于此认知,自19世纪起,沙皇俄国增强了对卫拉特部、喀尔喀蒙古僧侣及贵族阶层的渗透力度,并一度在喀尔喀地区成功获得了治外法权。
俄国基于此进一步策划了一系列间谍行动,鼓吹背离清朝,寻求自治,或是向沙皇俯首称臣并缴纳贡品。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长期以来对喀尔喀上层的僧侣与贵族进行收买、拉拢,并培养间谍的行为紧密相关。

事实上,众多推动外蒙古独立的核心人物是从俄罗斯领土逃逸至此的,他们所持有的武器装备同样大多源自俄罗斯。尤其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黑喇嘛”丹毕坚赞,他本就是俄罗斯出身,遵照俄国的指示潜入外蒙古,其沙俄间谍的身份确凿无疑。毋庸置疑,外蒙古的独立进程中,沙俄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总体而言,沙俄在其长达391年的历程中,主要表现为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记录,而中国则不幸成为了被沙俄侵占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
2015年5月18日,新华网报道,黑龙江省决定将某一政区名称恢复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永铭惨痛历史”。


配配查-按日配资炒股-配资行业查询-线上配资排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